
在这个时代的舞台上,虽然每个人从自身的逻辑出发都是合理的,但他们既无从预见,更无法控制这些相互冲突诉求所最终形成的合力,最终结果就是出现了一个事与愿违、让人瞠目结舌的严重后果。

我们所知的英国,早已不是以前那个“自由英国”了。自由放任原则曾给这个国家带来长久的繁荣,在对外开放、对内松绑的基础上,英国迸发出无穷的经济活力和创造力,不仅是“世界工厂”,也锻造了一个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商业帝国。然而,曾经使它成功的因素,在现代转型的艰困中却未能幸存下来,这无疑是一出悲剧,且是一出宏大的悲剧。
至于它什么时候失去这种自由的,一直以来争议倒也不大:通常都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是一个关键转折点,在那之后,为了适应一场全面战争的需要,英国人不得不打破其原有的传统和信条,在急迫的危机面前改造了自己的国家。
在大战的阴影下,英国人普遍感觉,在保护英国人免受攻击和威胁方面,政府做得太少,几乎对所有的领导人都失去了信心,可想而知,但凡无法响应这种需求的政治人物都在不断丧失支持。其结果,到1918年战争结束时,自由党已经分崩离析,因为“自由放任”显然无法满足全面战争的需要。事实上,这场战争尚未结束,就已经有人意识到,逝去的并不仅仅是在战争期间的那些死者,还有不少东西也永远地逝去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自由主义。
历史学家A.J.P.泰勒曾回望那过去的好时光:“在1914年8月以前,任何一个明智、守法的英国人都可以平稳地度过一生,除了邮局和警察,鲜有人会意识到国家的存在。他可以住在自己喜欢的任何地方,想住哪儿就住哪儿。他没有正式编号和身份证。他可以在没有护照或任何官方许可的情况下出国旅行或永远离开他的国家。他可以不受限制地把钱兑换成任何其他货币。他可以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购买商品,就像他在国内购买商品一样。”
当然,还不止这些,那是一次秩序重整,一次全面的价值重估,诸如自由贸易、进步主义这类原先神圣的信条已经被看作不合时宜,而这势必带来方方面面的震荡与重组。仅从这一意义上说,也可见自由英国不是突然死亡的,毕竟从旧有的状态调整到新状态势必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即便全面危机之下可能被压缩在短短数年内完成。
那甚至并不全然是战争带来的冲击使然——战争不是对自由英国的一次突然袭击,而是它那个早已开始的衰亡过程的终点,最多只是加速了它的死亡。英国记者、历史学家乔治·丹杰菲尔德在其名著《自由英国的奇异死亡》中所试图证明的,正是这一点:自由英国并非死于他杀,而是一次慢性自杀。全书开篇就说得明白:“战后十年间的诸般夸张行为,也许人们会觉得那是战争造成的,但实际上在战前就已经开始了。大战令一切都加速了,政治上的、经济上的,还有行为方面的,但大战并没有开启任何新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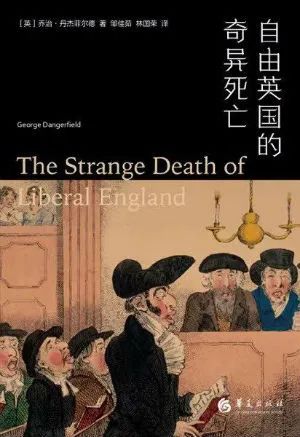
《自由英国的奇异死亡》
[英]乔治·丹杰菲尔德 | 著
邹佳茹 林国荣 | 译
华夏出版社
2024年1月

在谈到这个话题时,英国人并不像其它国家的人那么沉重。小说家E.M.德拉菲尔德早就曾不无戏谑地说过,英国人的重要信条之一,就是“英国正在走向灭亡”。那带有一种镇定自若又置身事外的奇怪感觉,仿佛是在谈论一件与己无关的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亲历者能看清自己的处境:那往往是属于后人的特权,而身处局中的人,就像古希腊悲剧中常有的那样,受无形的力量(有时被称作“命运”)主宰而浑然不知。
就此而言,对这段历史固然少不了客观陈述、理性分析,但将它呈现为一出宏大、诡异的悲剧,不仅引人入胜,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到这样一点:在这个时代的舞台上,虽然每个人从自身的逻辑出发都是合理的,但他们既无从预见,更无法控制这些相互冲突诉求所最终形成的合力,最终结果就是出现了一个事与愿违、让人瞠目结舌的严重后果。没有人试图有意识地杀死那个自由英国,但当英格兰精神中长期被压抑的东西爆发出来,自由英国注定无法幸存,尤其是它那种老派的优雅,无法容纳太多横冲直撞的新生力量。
直到1880年代,英国人在骨子里都可算是自由主义者,但在此后的短短30年间,脚下的地基地动山摇。在美国、德国这些后来居上、咄咄逼人的竞争对手面前,自由贸易的理想渐渐难以坚持,保护主义从未如此具有吸引力;国内政治也一样,以往那不过是绅士们严肃的游戏,但现在总有那么一点你死我活的硝烟味。那些原本边缘的力量,工党、爱尔兰自治运动、女权主义,到世纪之交也纷纷以好斗的姿态登上了舞台,尽管其做派有时令绅士们为之震惊,但现实证明,那种粗野的做法确实是奏效的。
但为什么说这是“奇异死亡”(strange death)?书中没有解释,似乎只是一些看上去难以理解的小事件恰好凑在一起,产生了某种神秘的共振效果,从而形成了摧毁旧框架的完美风暴,等到萨拉热窝的枪声响起,“一种无意识的、从灵魂深处喷涌而出的巨大能量”终于让它轰然倒塌。不过,这是呈现出来的表象,其内在的动力却不止如此。
自由英国的这一死亡,之所以说“奇异”,恐怕是因为其死因,正是由其自身所酝酿出来的。有必要注意的是,“自由英国”的英文是liberal England,而liberty一词虽然常被译成“自由”,但与那种特指自身言行的内在自由(freedom)不同,强调的是社会层面,一种个人从受压迫、受限制的状态中得到解放的“自由”。关键之处就在这里:“自由英国”的原则本身就肯定了这种个体得到解放的权利,因而看似吊诡的是,它最终的失败却恰好证明了它已成功地深入人心,那些边缘的群体起而反叛并寻求自身权利就是证明——它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
原本在和平年代里,这还不是大问题。自由党所倡导的理念被不同人群所接受,然而长期的社会繁荣酝酿了异质性越来越强的多元群体,自由党逐渐显得像是不可理喻的杂合体,以至于很难代表所有人的利益诉求。像工人、女性、爱尔兰人这样的群体如果说表现得更为激烈,那是因为他们尤为不满,原本整个社会秩序的大厦就建立在他们默默无闻的付出之上,但当他们觉醒过来却发现自己在现有秩序内没有真正的代理人。可想而知,这样一种秩序注定是难以为继的:要么调整秩序满足他们的诉求,要么就在低烈度的持续冲突中走向毁灭。

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当然可以把当时那些人夸张、激烈的举动看作是受非理性的力量驱使,但有必要指出的是: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合理的诉求恐怕是没有人会理睬的。被压抑的力量之所以表现出来如此可怕,正是因为它们被压抑、忽视太久了,而改革又太慢、太少,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
这是那种雍容的老派风格难以招架的,自由党虽然在一战前仍然勉力维持着议会多数,但明显已经左支右绌,只能通过对工党、爱尔兰自治等问题不断做出让步来妥协退让。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和他的上司、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一样,在面对复杂、危困的局面时,宁可选择观望而非主动出击,其结果是当他最终试图出面解决问题时,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那是自由英国的挽歌,昔日那种心平气和、安稳雍容和受人敬重的品性也随之消逝,对那些为之惋惜的人们来说,这意味着原先那种理性、克制、温和的贵族做派,被一种混乱、暴烈、躁动但生机勃勃的非理性力量所取代。严格来说,这诚然是自由英国的死亡,但换一面来说,也是民族精神生命的自我更新,至于这种更新到底是好是坏,那就取决于你究竟怎么看待了。
确实那也不尽然是坏事:就连作者,虽然明显对自由英国的衰亡抱有惋惜,但他也说了,“值得再次重申的是,在1914年的春夏,大英帝国呈现如此动荡的面貌,并不是因为死,而是因为生”——换句话说,自由英国的死亡,其实是新兴力量在喷涌,给英国带来重生,若非如此,它也无法迎接接下来的两场世界大战带来的严峻考验。
然而,那是有代价的。那种更加积极主动应对危机和挑战的政治力量,无论是什么主张,必然都会强化干预,如果人们以前抱怨自由英国做得太少,那么很快就会抱怨新的政府做得太多。正如后来担任英国首相的张伯伦敏锐指出的,“不幸的是,近年来,人们越来越依赖政府,把它作为劳资纠纷的最终仲裁者”。《凝视上帝:大战中的英国》在回顾这段历史后发现,“最严峻的情况是,这个国家膨胀起来,对人民的生活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控制。这场战争成为一个创建福利国家的契机,早在签署停战协定之前,政府就已经有了改善医疗、住房和教育的打算”。
这就是为什么要哀悼那个自由英国,因为它所代表的不仅是一种风格、一种礼仪,也是一种实践和可能,它确实有种种问题,但替代它的那个英国难道就没有吗?历史并不是怀旧者的浪漫癖好,历史乃是提醒我们:当我们面临类似困境时,是否能做出不一样的选择。














